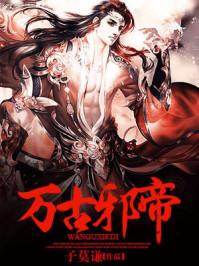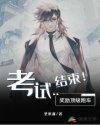笔下文学>短篇悬疑恐怖故事集 > 第272章 百草堂之金樱子(第3页)
第272章 百草堂之金樱子(第3页)
正说着,街对面忽然放起鞭炮,噼里啪啦的声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。孙玉国穿着件簇新的宝蓝色长衫,站在回春堂门口,手里举着个锦盒,对着围观的村民吆喝:“各位乡亲!看看我这‘西洋金樱子’!无刺无毒,效力是本地货的十倍!”他打开盒子,里面果然摆着些黄澄澄的果实,圆滚滚的像小橘子,表皮光滑,连个尖刺都没有。
“孙老板,这玩意儿真能治遗尿?”有人踮脚张望。
“何止遗尿!”孙玉国拍着胸脯,玉镯在手腕上晃得刺眼,“久泻、带下、腰酸背痛,通治!我这可是托人从西洋运来的,一两要价半两银子,今天开张,买二送一!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刘二狗穿着件新短褂,在旁边帮腔:“我上次吃了本地金樱子肚子疼,孙老板给了颗这西洋货,立马就好!神得很!”他故意挺了挺肚子,露出腰间的赘肉。
人群里一阵骚动,有几个曾被孙玉国骗过的村民将信将疑,但更多人被“西洋”“效力十倍”吸引,围了上去。
王宁站在百草堂门口,看着那盒黄澄澄的果实,忽然想起林婉儿说过的话:“药材的本性藏在形里,有刺的未必伤人,无刺的或许更毒。”他转身对张娜道:“你去芦苇荡时,顺便问问渔户,有没有见过这种无刺的果实。”又对钱多多说:“钱老板,劳烦你想法子弄一颗来,我得瞧瞧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
张娜挎着竹篮出门时,王雪追上去塞给她一把小剪刀:“嫂子,芦苇荡边的荆棘多,小心些。”小姑娘的辫子上换了根新的金樱子刺簪,是用云栖岭那株百年金樱子的刺做的,磨得锃亮。
王宁回到柜台后,铺开纸笔,写下“金樱子真伪辨”几个字。他想起祖父教的辨识法:一看刺,二闻味,三尝性。真金樱子有刺,闻着有涩香,嚼着先涩后甜;假货多半无刺,气味怪异,味道发苦或发腥。正写着,忽然听见门口吵吵嚷嚷,刘二狗带着两个汉子闯了进来。
“王大夫,别装模作样了!”刘二狗叉着腰,油乎乎的褂子敞着怀,“孙老板说了,你这本地金樱子是劣药,赶紧下架,不然我们砸了你的铺子!”
王宁放下笔,月白色长衫的下摆扫过药碾子,发出轻微的响动:“《唐本草》有云,‘药无贵贱,对症者良’。孙老板的西洋货再好,不对症也是毒药。”他指着墙上的告示,“我这金樱子,性味功效写得明明白白,敢让乡亲们查验。他那无刺的‘西洋货’,敢说清来路吗?”
两个汉子想上前掀柜台,被王宁拦住。他的手虽瘦,却像铁钳似的有力,那是常年握药锄、碾药材练出的劲。“想动粗?”王宁的目光扫过两人,“去年李老爹的风湿,是我用金樱子根治好的;前年张婆婆的久痢,是我用金樱子配白术救回来的。你们现在要砸的,是能救你们命的药铺。”
汉子们的手僵在半空,刘二狗还想撒泼,忽然看见钱多多领着个穿官服的人走进来——是县里的药监局吏。“王大夫,我把陈吏请来了。”钱多多的纱布又渗出血,“孙玉国卖假药,该管管了。”
陈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,穿着藏青色官服,手里拄着根用金樱子藤做的拐杖。他走到柜台前,拿起颗金樱子闻了闻,又翻看了王宁写的辨伪文,点点头:“王大夫说得对,金樱子以有刺为真。”他转向刘二狗,“去把孙玉国的‘西洋货’拿些来。”
孙玉国不情不愿地让伙计送了样品。陈吏捏起一颗,用指甲刮了刮表皮,黄颜色掉了些,露出里面的白芯。他又放在鼻尖闻了闻,眉头紧锁:“这是用硫磺熏过的山橘子,冒充金樱子!硫磺性热有毒,吃多了会伤肝肾!”
人群顿时炸开了锅。“我说怎么看着不对劲!”“难怪孙玉国神神秘秘的!”
孙玉国脸色惨白,还想狡辩,被陈吏打断:“上个月邻县就查过这种假货,骗了不少银子,没想到你敢弄到百草镇来。”他让人把孙玉国和假金樱子一起带走,临出门时,拍了拍王宁的肩膀,“你祖父当年教过我辨识药材,说金樱子的刺是‘护药之锋’,没了锋芒,就没了药性。你守住这锋芒,好。”
刘二狗早就溜得没影了。药铺里,王雪正帮钱多多换纱布,张娜挎着竹篮回来了,篮子里装着些芦苇荡采的金樱子,虽然个头小,却带着新鲜的露水。“那边的金樱子长在水边,刺更密,性更涩。”她把果实倒在筛子里,“陈吏说,孙玉国被押去县里了,回春堂要查封。”
王宁望着窗外,夕阳把百草堂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拿起颗芦苇荡采的金樱子,刺比云栖岭的更尖,扎得指尖发麻。“这刺啊,”他忽然对王雪和张娜说,“看着扎人,其实是在护着里面的甜。就像做人,得有点锋芒,才能护住心里的仁。”
钱多多看着王宁写的“金樱子真伪辨”,忽然道:“王大夫,这文章该印出来,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王宁点头,目光落在药书的扉页上,那是祖父写的话:“药有锋芒,医有仁心,锋芒护仁心,仁心驭锋芒。”他拿起笔,在文末添了句:“金樱子刺虽锐,不伤善者;假药看似柔,却藏剧毒。”
暮色渐浓时,张娜点亮油灯,灯光映着满柜的药材,金樱子的涩香混着油灯的烟火气,格外安稳。王雪在碾药槽里磨着金樱子,轱辘声里,王宁忽然想起林婉儿的话:“涩不是滞,是收;锐不是凶,是守。”
或许,该去云栖岭看看被砍的金樱子——说不定根还没断,明年能发出新芽。毕竟,带着刺的生命,总比光滑的假货坚韧得多。
腊月初的寒风卷着雪籽,打在百草堂的窗纸上沙沙作响。王宁正坐在柜台后分拣药材,面前摊着几堆金樱子——有云栖岭幸存的老株果实,紫黑发亮;有芦苇荡采的水边品种,刺密而尖;还有林婉儿托人送来的深山干货,个头虽小,却带着股陈酿般的醇厚药香。他用竹镊子仔细挑去果实里的碎刺,指尖在冷空气中冻得发红,却依旧稳当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“哥,张嫂子说街口的李木匠家,娃又拉又吐,烧得厉害。”王雪裹着件厚棉袄跑进来,辫子上沾着雪沫,“她男人去请孙玉国,回春堂关着门,说是被查封后还没开呢。”小姑娘跺了跺脚上的泥,怀里抱着个暖炉,炉边放着刚熬好的金樱子茶,“张嫂子让我问问,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去看看?”
王宁放下镊子,月白色长衫的袖口沾着些金樱子的绒毛。他摸了摸妹妹冻得通红的鼻尖:“雪丫头,把药箱备好,带些金樱子、黄连、木香,再拿两贴退烧的膏药。”他起身时,腰间的药囊晃了晃,里面装着常年不离身的急救药材,“告诉张嫂子,我这就去。”
张娜从后堂出来,手里拿着件厚棉袍,非要给王宁披上:“外面雪大,你上月风寒还没好透。”她帮他系好腰带,指尖触到他背上的旧伤——那是年轻时为采悬崖上的金樱子摔的,“记得带上林姑娘给的方子,她说治急症得用猛药,但金樱子的涩得收得住才行。”
药箱沉甸甸的,装着陶罐、药秤和用油纸包好的药材。王宁踩着积雪往街口走,棉鞋踩在冰上咯吱作响。路过回春堂时,见门板上贴着封条,积雪在台阶上堆了半尺高,想起孙玉国被带走时的狼狈相,心里竟没什么快意,只觉得空落落的——同行相轻到不顾人命,终究是丢了医者的本分。
李木匠家挤了不少人,烟气弥漫得让人睁不开眼。孩子躺在土炕上,小脸烧得通红,嘴唇干裂起皮,时不时抽搐着呕吐,吐出的东西带着酸腐味。李木匠的媳妇坐在炕边抹泪,见王宁进来,“扑通”就跪下了:“王大夫,你救救娃吧!再这么拉下去,小命都要没了!”
王宁赶紧扶起她,放下药箱就往炕边凑。他摸了摸孩子的额头,烫得吓人,又掀开被子看了看孩子的手心——布满红点。“什么时候开始的?”他一边问,一边取出银针,在孩子的虎口和足三里扎了两针,手法又快又准。
“昨天后半夜,”李木匠搓着手,声音发颤,“先是喊肚子疼,然后就上吐下泻,村里已经有好几个娃这样了,都说……都说像是痢疾。”
“痢疾?”王宁心里一紧,又给旁边一个同样患病的孩子诊脉,脉象洪数,舌苔黄腻,“是湿热痢,得清热燥湿,还得涩肠止泻,不然拉脱水就危险了。”他打开药箱,取出黄连和木香,“这两味药先煎,去湿热。”又拿出金樱子,“这个后下,固肠道,别让正气泄得太厉害。”
张娜不知何时也来了,正帮着烧火煎药,素色布裙沾了不少柴灰。“我刚才去别家看了,”她压低声音对王宁说,“好几户都有娃发病,怕是要传开。”她往药罐里加了些姜片,“要不要去告诉陈吏?”
王宁点头,让李木匠去报官,自己则守在药罐边。药香混着烟火气在屋里弥漫,黄莲的苦、木香的辛、金樱子的涩,奇异地交融在一起。他想起林婉儿给的方子——“痢无止法,当通因通用,然泄久必虚,需涩以固之”,此刻才算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。
药煎好时,孩子已经烧得迷迷糊糊。王宁用小勺一点点喂药,苦涩的药汁沾在孩子嘴角,他就抹点提前备好的金樱子蜜膏——那是张娜用金樱子果肉熬的,甜中带涩,正好压苦。喂完药没多久,孩子的体温果然降了些,不再抽搐,呼吸也平稳了。
刚松口气,就见陈吏带着几个医官匆匆赶来,官服上落满雪花。“王大夫,县里刚接到消息,周边几个镇都闹起了疫痢,怕是要封镇。”陈吏的脸色凝重,手里的金樱子藤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,“你这方子管用吗?能不能推广开?”